
首頁- 新聞中心- 黔圖匯- 人才網- 視聽中心- 專題- APP

 新聞熱線:0855-8222000
新聞熱線:0855-8222000
因走鄉村旅游高端與民族文化保育并行路線而名聲大振,卻因實際旅游收益不高而受村民質疑。是堅守“品質”等待高端市場成熟,還是放低“身價”迎合大眾消費需求?作為一個有著700多年歷史的古村落,地捫村的人們正面臨一個新課題——
位于黎平縣茅貢鄉的地捫是侗族地區民族風情文化保存較為古老完整而且最具有代表性的侗族村寨。
黎平縣已與香港明德創意集團簽訂了合作協議,地捫正在探索發展侗族國際生態旅游的品牌模式。
在貴州,像地捫這樣具有600年以上歷史的文化村落景觀就達1800個。
那么,如何保護和可持續利用這些豐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遺產,如何根據當地情況尋找到一個科學的多元的發展和保護模式,是地捫面臨的困惑,同樣也是這些村落正在面對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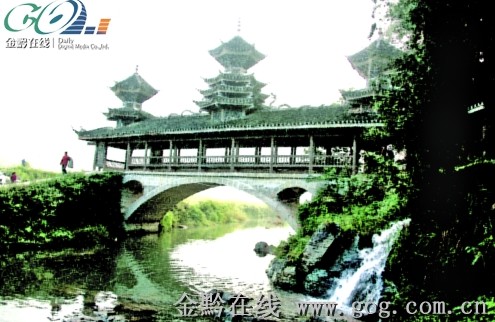
圖分別為地捫風雨橋的素描與水彩效果圖。
新聞背景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貴州居民留下了眾多豐富多彩、獨具民族特色的村落文化景觀,可以數上名來的寨子成千上萬,具有600年歷史的文化村落景觀就達1800個。
寨子是貴州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國務院公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貴州共有62項,約占全國總數的6%;貴州已公布兩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數量達297項。
而這些都活在貴州的少數民族寨子里,活在民族文化傳承人的心里。
但是,當走入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語境,村落文化景觀面臨挑戰,旅游工業化的發展給寨子遺產保護帶來一種單一的發展參照,一些寨子不是盲目模仿10年前的麗江發展模式,就是跟著后工業文明的步伐,快速開采和挖掘民族民間文化,造成文化的掠奪性開采,使得民族村寨的發展處于一種單向的趨同旅游工業的發展模式。
這些村寨該何去何從?地捫正在探索屬于自己的出路。
在發源于侗戲之鄉——黎平縣茅貢鄉的清水江支流源頭的大山深處,有一個古樸迷人、風情濃郁的侗寨——地捫。
地捫在貴州眾多的村落中顯得很獨特,在外界它因神秘、原生態而廣博好評,正在其內部進行的鄉村旅游高端模式探索——文化保育與旅游開發共生,讓人們看到它的探索價值,并為之感到欣喜。
然而在當地人眼中,它卻是叫好不叫座,沒有帶來所預期的現實旅游經濟收入而遭受質疑。在其堅持的貴州鄉村旅游高端路線上,來自現實的矛盾,開始讓這個具有標本意義的村落感到艱難和困惑。
矛盾 磚房木房看長看短
5月中旬,一件發生在地捫村的事驚動了縣里:村里有30多戶人家強烈要求拆掉侗族民族風格的老木房,建新式磚房,為此與村委會僵持不下。
此事引起黎平縣高度重視,專門派出工作組駐村做群眾思想工作,“雖然目前是勉強做通了他們的工作,暫時不建磚房,但是不知道能堅持多久啊?”一位駐村工作人員說。
一個在貴州大步前進開發鄉村旅游過程中常見又難以解決的問題——傳統民族文化保護與現代化的矛盾在地捫村又出現了一次激烈的對抗。
有別于以往其他一些村落那種順其自然的發展,似乎從一開始就在各方努力下想規避這個矛盾的地捫,還是走向了這個大家都不想面對卻又不得不面對的局面。
地捫為何如此特別?大家為何對它抱有比別的村落更高的期待?
一切皆因地捫選擇了一條與其他村落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走鄉村旅游高端與文化保育并行的路線。
這似乎是一個近乎完美的解題,能夠很好地回答貴州眾多正在進行旅游開發或者已經開發了的村落的后續發展問題。
但現實是,探索進行得并不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順利。“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旅游沒有發展起來。”一位當地人直言不諱地指出。
自2010年起,記者在對地捫進行了連續4個黃金周追蹤調查后發現,當地旅游業的經營狀況顯然和地捫的名氣形成了巨大反差,4個黃金周里,地捫實際接待游客不超過100人,吃住在村里,產生旅游消費不超過80人。以該村鄉村旅游合作社開出的房費標準168元每間(標間)計算,4個黃金周整個地捫村的旅游住宿收入不會超過50萬元,其中還有一些是來自上級部門的接待安排。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地捫旅游業沒有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樣發展起來,不能帶來實際而豐厚的經濟收入猶如一個導火索,讓大家對以保留侗族民居原生態風貌促進旅游發展的做法產生了質疑。
記者了解到,在當地保護一棟具有幾十上百年房齡的老房子是一件很費心力的事。在黔東南農村,火災是木房最大的威脅,今年地捫已經有數棟木房失火。
在地捫的村規民約中規定,導致火災的人家不論是什么原因失火,都要遭到嚴厲懲罰:不僅要宴請全村人賠禮道歉,并且要遭到驅逐,3年內不準回村建房居住。
而在地捫成立鄉村旅游合作社之初,形成的一個決議是保護傳統民族文化(包括老房子),文化保育與旅游開發并行,并形成以原生態文化打造旅游核心競爭力的發展思路。
如今,旅游業的現狀顯然離村民們的期望值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守著一個并不能給他們帶來多少實際好處的古董木房子,有能力改善居住條件的村民,自然產生了修建新式磚房的想法。
建磚房風波,無疑將當地旅游發展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激化出來。
那么地捫進行的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它的鄉村旅游高端路線是什么樣?是如何與文化保育并行的?
探索 保護開發如何兩全
這似乎已經是一個古老的命題:當傳統文化遭遇現代化,當民族文化保護遭遇旅游開發。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府乃至民間,有大量人士為之奔走、思考、呼吁,甚至實踐。
地捫進行的探索,就是這樣一種實踐。或許從一開始,他們不是以此為目的,但在實踐過程中的矛盾呈現,卻是他們必須拿出勇氣和對策去解決的現實命題。
記者曾前后兩次赴地捫采訪,并持續關注那里的情況,所了解到的信息是:在地捫村,文化保育與鄉村旅游開發這兩條線分別由兩個機構推動進行,他們分別是地捫生態博物館和地捫鄉村旅游合作社。
2005年,由香港西部文化生態工作室投資興建的地捫生態博物館開館。
按照專家設計,博物館將發揮4個主要功能:一,成為古村寨歷史、文化、建筑、技術、環境、自然等變遷史的展示中心、研究中心、資料中心和對外學術聯絡中心;二,是原生態文化藝術和手工藝推廣傳承和當地社區鄉土教育的中心,以及當地居民的文化活動場所;三,是相關學術研究機構的研究基地和與當地聯系的紐帶;四,是接待旅游者住宿和交流當地手工藝品的商業點。
作為一家非政府機構,在當地5年多的建設推進中,有些功能作用發揮如預期推進——如其功能設置的前三點,文化保育工作在當地漸入村民生活,并且顯現了積極作用。
但是,專家設置功能的第四點——接待旅游者住宿和交流當地手工藝品的商業點,后來卻由之后成立的地捫村鄉村旅游合作社履行。
據地捫鄉村旅游合作社總經理兼地捫村黨支部書記吳勝華介紹,該合作社是在村民自愿基礎上組成,村民可以以老民居、土地、人力入股,成立鄉村旅館,出售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藝旅游商品,最后所得收入則按照股份進行分配。
于是在現實摸索過程中產生了如此模式:分別由兩家分工明確的民間機構——地捫生態博物館與地捫鄉村旅游合作社承擔了地捫的文化保育與旅游發展職能。
在地捫生態博物館推動下,部分居民參與了生態博物館的活動,侗族大歌、侗戲表演、原始造紙技術、傳統紡織印染技術、刺繡技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在村寨得到很好的傳承。
地捫村村主任吳世茂告訴記者,他的女兒原本在廣東打工,因為侗歌唱得好現在回村了,擔任村里侗歌表演隊演員,每月有一定的收入,雖然比在外面掙得少了,但方便照顧孩子和老人,還有家里的田土。現在像他女兒這樣的,村里還有好幾個。
因地捫生態博物館文化保育的努力,讓外界看到了地捫的價值:原汁原味的民風民貌,如世外桃源的鄉村寧靜生活,正是全球工業化背景下的稀缺人文與自然生態資源。
2010年“五一”黃金周,記者第一次去到地捫采訪,就為這個閉塞小村的高端旅游存在而驚嘆!
同年“十一”黃金周記者第二次赴地捫采訪時,遇到了一對從北京遠道而來旅游的夫妻,他們共同的感覺是:地捫比他們想象的感覺還要好,這里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讓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覺,他們的到來仿佛是對地捫生活的打擾,回到北京,他們不但不會大肆宣傳地捫,反而要好好地把它“藏”起來。
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撥游客在村里流連忘返,專門花錢請村里的歌師表演侗族大歌。
似乎對于地捫的一切,都有讓旅客驚艷的地方,來自貴陽的游客羅倩云對記者說,這里的鄉村旅館硬件很好,床很舒服,比起別的地方168元的房價雖然貴了些,但是能夠承受。
按照常理,受到游客如此青睞的地捫,應該引來旅游業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才對,但事實上,地捫接待的游客寥寥。
進退 地捫實踐考量現實
有當地人直接指出,是高端定位嚇走了游客。
那么地捫選擇的鄉村旅游高端路線到底有多“高”?
除了地捫能夠提供給游客的高質量侗族原生態文化生活感受,記者了解到,鄉村旅游合作社所屬的鄉村旅館設計標準是原生態休閑木屋風格的三星級酒店標準,房價定價168元/間。由地捫生態博物館提供入股的一棟單體別墅標價為3888元/天,其內部陳設堪比五星級酒店。
高房價顯然如一個門檻,將部分低端游客拒之門外。
記者第二次采訪地捫時,就有一撥游客走馬觀花般看過地捫就離開了,還有一撥是選擇了在村里的小學校扎帳篷夜宿。記者采訪了解到,其房價3888元的別墅至今入住的房客幾乎都是政府部門接待的客人。
直到后來記者采訪結束離開地捫,才恍然大悟,為何我們所住的鄉村旅館房東吳章權會在樓下魚塘喂魚時注視我們,原來是為有游客入住而高興,這意味著他的旅游收入將有所增長。
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目前地捫的游客量,顯然不可能給當地村民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
地捫的堅守,還能持續多久?
記者在與村口雜貨鋪老板吳章成聊天時得知,來地捫的所有游客都必須由鄉村旅游合作社統一接待,村民不能私自接待散客。
“那些游客覺得合作社的房價高了,飯貴了,我們卻不能接待,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走。”吳章成頗為激動地說,“我們可以把價格降低下來啊,這樣就不會流失游客了。”他指了指雜貨鋪右邊一棟民房說,那家人把房子拿來入股,但房價高了,沒人住,一個月就只一兩個人住,按照合作社提70%,個人提30%的原則,每月就百把塊錢的收入。
而面對部分村民的質疑,地捫生態博物館副館長張占賢卻表達了另外一種觀點:大量廉價游客的到來,必然會對村里的人文生態產生破壞。如果這樣,地捫將淪落到與被旅游開發破壞掉的村落一樣的境地,地捫也將失去個性,喪失掉未來的競爭力。
兩種思維各自代表了兩派不同觀點的村民,呈現了現階段地捫的矛盾和困惑,而這樣的矛盾也一直穿插進行在地捫的整個探索過程:一方面持續不斷而來的學術研究機構、專家學者、民間機構參觀學習,做研究;另一方面卻是游客寥寥無幾,旅游業的慘淡經營。
有當地人介紹,堅持走鄉村旅游高端的做法得到了很多前車之鑒的啟示。
一個現實的例子就是肇興,在當地政府大量引入外資進行旅游開發的同時,當地村民從中獲利微薄,于是產生了抵觸情緒,拆民居,拒穿民族服裝,當地人的感覺是——保護民族文化只是為了給外人謀利。
按照地捫生態博物館館長任和昕的理解,地捫的發展模式應該借鑒不丹,寧缺毋濫,做成旅游業的稀缺資源。
作為世界奢侈游的一個代名詞,不丹以其昂貴的消費為游客提供的是超一流的享受。“地捫具有這樣的資本嗎?”一位游客不禁發出疑問。
“像地捫這樣的地方,也許根本就不適合發展旅游業。”地捫生態博物館副館長張占賢說。
記者不由想起前后兩次采訪地捫的迥異感受。
第一次走進地捫,一位接受采訪的鄉干部告訴記者,自地捫走鄉村旅游高端路線后,僅半年時間旅游收入已經是之前3年的總和。這讓記者不由為地捫的模式感到無比欣喜。
但,在本是旅游旺季的黃金周,記者在地捫卻沒有見到一個游客,不由在內心留下了一個大大的疑問。
當年“十一”黃金周,為一探究竟,記者二赴地捫采訪。通過實地走訪村民,記者了解到,地捫的旅游經營收入其實十分慘淡,與地捫在外的巨大知名度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當談及西江苗寨,對其一個黃金周即有上千萬元的旅游收入,村民羨慕之情溢于言表。
按照地捫模式的原來設想,文化保育與發展鄉村旅游高端原本應該是兩個互為促進的因素。當文化保育成功了,原生態文化將會成為吸引高端游客的一塊磁石,打造出地捫村的核心競爭力,進而直接促進旅游業發展。
另一方面,當旅游業發展了,村民意識到保護古民居、保持民族文化傳統等等能夠帶來經濟效益,改善生活,必然會珍惜自己的文化資源,自覺加以保護。二者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
但事實是,走高端發展路線的地捫目前卻遇到了與肇興一樣的問題,發生在不久前的建磚房風波就是一次兩種觀點的現實激化。
但無論地捫的鄉村旅游高端探索會在現實因素的左右下向何種方向發展,他們的努力都已經在現實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向前,堅持到底,或許地捫果真就能突破現階段困惑。當地捫的高端度假勝地形象在市場上成功樹立,那么地捫旅游的春天也就指日可待!
退后,或許在現實左右下,地捫可能會改變高端旅游經營策略而降低門檻,獲取眼前的現實利益。
但不論是哪一種選擇,均對正在大步前進進行鄉村旅游開發的貴州具有標本意義。
更何況,地捫的前進方向還存在不可預料的可能。(羅梅)


凡本網注明“來源:黔東南信息港”的所有作品,均為黔東南信息港合法擁有版權或有權使用的作品,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黔東南信息港”。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黔東南信息港)”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