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艾滋病重型犯監獄 警察自嘲是地下工作者
[導讀]坊間傳聞,艾滋病是“免罪金牌”是否屬實?對于艾滋病罪犯,警察如何進行有效監管?這群重新犯罪率超過30%的艾滋病罪犯,他們在高墻里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警察通過掛在監舍門口的“心情晴雨表”隨時了解罪犯情緒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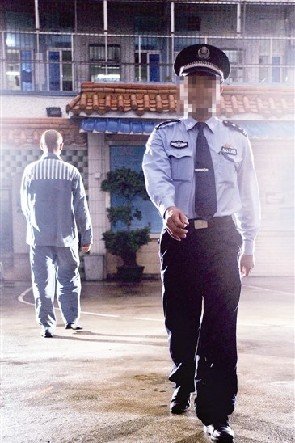
傍晚,高明監獄十六監區一位獄警與罪犯結束談心
佛山市高明區一處偏僻的村落,在崎嶇的鄉道將盡之處,一棟古舊但卻整潔的院子跳進記者眼中。
這里是高明監獄的十六監區。有人說,這里是神秘高墻內最為神秘的地帶。從2006年6月開始,廣東省一部分艾滋病重型罪犯關押在這里。
坊間傳聞,艾滋病是“免罪金牌”是否屬實?對于艾滋病罪犯,警察如何進行有效監管?這群重新犯罪率超過30%的艾滋病罪犯,他們在高墻里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南方日報記者穿過嚴密的隔離護欄,探訪高墻內最神秘地帶。
坊間傳聞艾滋病是“免罪金牌”,純屬子虛烏有
鐵門緊閉的監倉走廊上,十多名罪犯正在放風,或蹲或坐,見有外人進入,其中幾個起身探頭觀望,眼神迷離,在警察的提醒下,又回到原位,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煙。
這是記者穿過監區鐵門、進入高明監獄十六監區監舍時見到的第一幕。
這時,一名警察正在操場上組織罪犯進行隊列訓練,幾名警察站在邊上看守著另外一部分罪犯活動。操場并不大,有乒乓球臺和其它一些設施。
在高明監獄十六監區,集中關押重型艾滋病罪犯,高危病人加重型罪犯的雙重身份,讓恐懼的氣氛一度彌漫。
據了解,自2000年起,全省有20多所監獄開始零散收押艾滋病罪犯。之后,為了方便管理,全省艾滋病罪犯集中關押在樂昌、東莞、女子監獄和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高明監獄是其中之一。
省監獄管理局局長于保忠告訴記者,起初艾滋病罪犯如何關押成為監獄監管的難題,監獄對艾滋病罪犯關押條件有一定難度,不能為艾滋病罪犯提供相應的醫療條件;另外從警察到其他普通罪犯對艾滋病罪犯有畏懼心理。但是他強調,坊間傳聞艾滋病是“免罪金牌”純屬子虛烏有。
于保忠介紹,監獄收押艾滋病罪犯,一種是從看守所轉入監獄時就被檢查出患艾滋病,疾病診斷證明齊全的,另一種則是偏遠貧困地區看守所沒有條件對嫌疑犯進行艾滋病毒檢測,罪犯到監獄后才被檢測出來的。“按照有關規定,監獄均予收押。”
免罪一說無根據,但是對艾滋病罪犯區別對待倒是真的。
記者看到,監獄每個監舍門口都掛了一塊“心情晴雨表”,分別用頭像表情標明“高興”、“一般”、“低落”三種情緒。每個罪犯都可以通過移動卡位隨時告知警官自己的情緒變化。監區警官介紹,這是為了每天能及時掌握罪犯的情緒變化。
十六監區監區長楊小哇告訴記者,由于艾滋病罪犯身體素質差、病情不穩定,管教模式與普通監區不同。“很多罪犯得知病情就像被宣判了死刑,有的罪犯甚至無法接受事實,當場暈了過去。沒了自由,沒了健康,人生最寶貴的兩樣東西一下子全丟了,不少罪犯對人生失去積極的態度,不少人有自殺傾向”。
回歸社會難
艾滋病罪犯保外就醫成功率僅為3%,重新犯罪率卻超過30%
絕望、焦慮、敵視、恐慌,這是專管警察總結出艾滋病罪犯的常見心態。在高明監獄十六監區,因吸毒入獄的就占到92%。“這些人基本都淪落到被家人、社會拋棄的地步,即使刑滿出獄后,還是會重操舊業”,楊小哇告訴記者,這個監區罪犯的重新犯罪率超過30%,很多都是“二進宮”、“三進宮”的累犯。
罪犯李某(化名)就是一名“二進宮”累犯。2010年11月,李某因犯搶劫、搶奪、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入高明監獄十六監區服刑。然而這時他剛出獄還不到2個月。
面對記者,李某平靜地回憶往事,而對于所有犯罪的細節,他一律以“忘記了”一筆帶過。
1994年,17歲的李某輟學跟著一群老鄉在深圳某物流公司任運輸司機,拿著每月一萬多元的高薪。物質富足后,他不慎染上毒癮。“1000多元一克的海洛因,我一次就買2000塊錢的。”
2004年,李某發現自己染上了艾滋病,絕望的李某開始為了毒資搶劫,后被判在陽春監獄服刑,2010年9月刑滿釋放。
決心重新做人的李某出獄后,剛回家就被父母趕出家門,只能在自家后山上搭起茅草屋度日。在此期間,他曾考慮到一家工廠打工,然而,上班第二天老板一得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立刻給了他雙倍工資把他辭退。心生仇意的李某開始瘋狂報復,在短短一個半月里,先后參與搶劫、盜竊、強奸等作案四次,最終被公安機關抓捕。
李某說,現在最讓他牽掛的是他11歲的女兒,但是見與不見,想與不想,現在已變得不重要,只希望在監獄里的每一天都過得開心。他坦言,自己的后半生大概是要在監獄度過了。
擺在艾滋病罪犯面前還有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他們的回歸社會之路普遍漫長而曲折,這突出表現在艾滋病罪犯的保外就醫、減刑假釋成功率極低。
罪犯伍某沅(化名),因搶劫罪被判處三年半有期徒刑。今年8月,因其改造表現良好,高明監獄為他向其所在社區提請假釋。然而,當地司法局、司法所、派出所、村委會均以該犯可能會危害社會或無監管照顧條件為由拒絕接收。
另外一名罪犯巫某平(化名),今年9月艾滋病情加重,突發急性腦膜炎危及生命,監獄啟動緊急保外就醫,并向其家人下達病危通知書。然而,由于無法承受家人、鄰里對艾滋病的恐懼和排斥,巫父拿到病危通知書那一刻,只淡淡說了一句:“生與死,都交給監獄吧!”
據統計,自2006年以來,高明監獄曾為26名符合條件的艾滋病罪犯提請保外就醫,最終只有3人成功獲保。而全省艾滋病罪犯保外就醫的成功率僅為3%,遠低于其他病犯的近100%。“回歸社會會遭普遍性拒絕,艾滋病罪犯很少主動提出保外就醫,待在監獄里更安心。”有警察如是說。
監管風險高
零距離接觸引發職業暴露風險,警察自嘲“地下工作者”
高明監獄監獄長王培文告訴記者,目前艾滋病罪犯監區管著全監3%的罪犯,卻承擔著90%的安全風險。
去年8月的一天,監區指導員王警官在一樓值班,突然聽到二樓監舍傳來一陣激烈的吵鬧聲,監控視頻顯示二樓監倉里,一名犯人手持鐵片,劃傷腦袋滿臉是血正嗷嗷大叫,狹小的監舍一片慌亂。
王警官一個箭步跑上二樓,打開監倉鐵門,沖到了這名患有精神病的罪犯李某面前,安撫當事人情緒,了解事發情況,隔離疏散其他犯人,順勢抓往罪犯的手,奪過鐵片。
“當時不覺得什么,事后還是覺得害怕。”王警官回憶,事發現場罪犯李某滿臉是血,情緒激動,不時還用手抹去蒙在眼前的血,然后隨手就是一甩,血濺得到處都是,如果當時李某的血灑到了他人的眼睛,那情況可就嚴重了。
監區長楊小哇經常提醒同事,如果身體有傷口,一定要包扎好,防止在與病犯接觸過程中感染病毒。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監倉值班的十多名干警中,就有3人手腳等不同部位貼著止血貼。
然而,艾滋病犯的并發癥才是對警察健康最大的威脅。記者了解到,一些病情較重的艾滋病犯由于免疫水平低下,很容易出現并發癥,如大部分艾滋病晚期犯人都會出現皮膚潰爛,并發肺結核、肝炎等傳染性強的疾病。
“我們想買保險都沒人愿意接。”楊小哇說,監獄曾多次聯系保險公司想為警察多買一份特殊行業人群保險,但保險公司的業務人員一聽到是艾滋病犯監區的警察,立刻就拒絕了。
在警察之間,他們常自嘲為“地下工作者”——監區大部分警察都沒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在監獄從事的實際工作,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采訪中,記者遇到一名剛剛大學畢業主動申請到艾滋病監區工作的警察,采訪結束時,他反復叮囑記者稿件中不要出現他的姓名:“我還沒有結婚,不想給未來的家人帶來困擾。”
針對艾滋病罪犯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事件和違紀行為,監獄分別制訂應急處置專項預案,“隔離不隔絕,重視不歧視”是高明監獄這幾年總結出來的經驗。
記者走訪發現,即便是在高明這樣具備集中關押艾滋病罪犯條件的監獄,監舍主體都是上世紀70年代建成的破舊房屋,有的甚至是危房,連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承受力都無法滿足,無奈之下,警察只能每天提著熱水瓶幫罪犯打開水洗澡。硬件設施的落后為監管安全帶來了極大隱患。
省監獄局表示,目前的經費勉強可以滿足所需,但隨著罪犯人數的增多,監獄監管設施落后和監舍緊張的矛盾日益凸顯,政策扶植的缺口集中在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