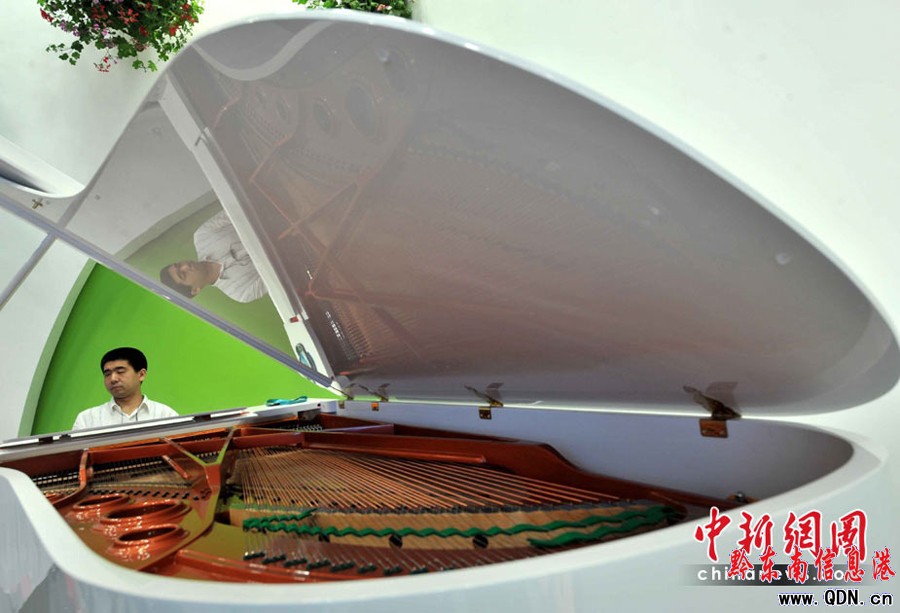云南山村172戶居民因干旱舀泥漿水生活(圖)

一會兒工夫,小水潭里的水就被取光了,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滲出水來。本報特派記者 郭建政 攝
大眾網--齊魯晚報 云南省曲靖市龍慶鄉大杜吉村,位于海拔1800余米的深山里。大旱讓這個村子了無生氣。兩個月來,無助的村民只能從村里僅剩的兩個小水潭里舀泥漿水來生活。62歲的老村支書龔玉春痛心疾首,30年來他一直希望幫助村里鉆一口井。
兩處小水潭是僅有的活水
從曲靖市師宗縣城出來,國道盡頭是省道,柏油路盡頭是水泥路,水泥路盡頭是土路,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窄,龍慶鄉的大杜吉村就藏在這海拔1800余米的深山里,宛如置身孤島,送水車難以駛入,村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自救。
上午11時,村子一竹林底下的小水潭沁出了一些水,龔玉春讓兒媳婦趙紅英去舀回來,這是村里僅有的兩處活水之一,是全村172戶人家的生命之源,村民圍著沁水口用石頭壘成深井。一個上午,小水潭積了約4桶水,趙紅英幾瓢下去,勉強舀夠半桶清水,被攪起的泥漿已讓小水潭映不出她的倒影,但她還是繼續把桶舀滿。
歇一會兒,就提著桶去看看沁了多少水,這已是大杜吉村村民的自覺意識。村子缺水兩個多月了,村民只能等著水沁出來,不管渾濁與否,一瓢不剩地舀回家,沉淀上三四個小時就用,而每次打水都得先抹掉桶底沉淀的厚厚的泥漿。
云南的天亮得晚,早晨5點半,水潭邊就已經擺滿了桶,擠滿了人。小水潭并不爭氣,沁了一夜,也沒給村民更大的希望,先到者舀清水,后到者舀濁水,眼看著只有幾桶水的存量,村民們心照不宣,并沒有將自己的桶舀滿。
龔玉春說,為了這點兒水,村里80多歲的老人夜里三點就來等了。龔玉春額頭上日益增加的皺紋,似乎也在勾畫著“井”這個字。
村民集資打井是“干棍子擰水”
龔玉春早就想幫村里打口井。1988年,他開始當村支書,給村民的承諾是拉電、修路,還有最重要的打水井。村子距鄉里有14公里的山路,1994年的時候通了電,不算慢;公路也一節一節地修到了村子里,不算寬,卻也夠村里年輕人騎著摩托車上下飛馳。但是水井呢,一直不見蹤影。
“天干一塊糖,下雨一包膿。”龔玉春用60年與紅土地打交道的經驗,形象地總結了紅土含水性差的特質。他說,一下雨,泥土就化作泥漿,天乍一放晴,地里馬上板結,水分丟盡,無法耕犁,在靠天吃飯的大杜吉村,干旱是個常態,村里沒有穩定的水源,家家戶戶都在門口蓋蓄水池,收集雨水。
龔玉春把記者拉進屋,從抽屜里取出一份打印文件,上面寫著“龍慶鄉大杜吉村打井可行性報告”,落款日期是“2000年元月”,上面蓋著“云南省地質工程勘察院”的章。
“沒有錢,村子太陡了,打井你們自己想辦法。”跑遍了鄉里,還跑了縣里的水建局等單位,龔玉春得到的答復無不如此。前來現場考察的各部門領導,走了一撥又來一撥,最終也沒有批準打井這個事。
云南省地質工程勘察院2000年出具的可行性報告顯示,根據對當地巖層的分析,村民出工出力,只需打井150米,花費17.66萬元就可以得到當地人世代渴望的充沛水源。
然而,10年過去了,打井的愿望終究沒有實現。靠村民集資,龔玉春說:“那是干棍子擰水,這里彝族和漢族雜居,是全國有名的貧困村,都是種莊稼的,哪有錢。”
牛羊死去,蓋樓因缺水停工
7年前,做了15年村支書的龔玉春不再連任。28歲的小兒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在曲靖至今沒找到工作,他無暇過問,他的心思還在這口井上,“村里一天沒有井就不行。”
沒有水,山上的草枯了,玉米不收,秸稈也少了,牛羊只能吃一些地里種的用以改善土質的被當地人稱為“綠肥”的草,或發生脹氣,或中毒身亡,村子里收購殘牛羊的廣告越寫越多;沒有水,許多正在蓋的小樓房成了“爛尾樓”,彭石橋家里的樓房剛用紅磚砌完一層就趕上大旱缺水,被迫停工,無奈之下,他出外打工,給媳婦扔下個爛攤子;沒有水,婦女把堆了一個多月的臟衣服稍稍打濕搓上洗衣粉,過一遍水了事,洗完臉、再洗完頭發的水溶有化學物質,還要留著和豬食。
看著66歲的何菊英老人背著比自己身體粗不止一倍的水桶,去小水潭舀泥漿水,然后晃晃悠悠地回家,龔玉春感慨萬千。他說,也有人開始下山去鄉里、縣里安家,老人在這里住了一輩子,不知道只有這里才缺水吃,大多數還是留在了這兒。
龔玉春每天晚上都等著看新聞聯播,看惠農政策里有沒有提到打井的內容,他說過段時日,他想再下山去找找有關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