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且蘭古國到仙都鎮遠
黔東南是古老的,千年的歷史傳承始終不變;黔東南也是開放的,州委、州政府著力打造的旅游這個朝陽產業,讓被稱為“人類疲憊心靈棲息家園”的黔東南向世界敞開了懷抱。
前世的歷史與今生的開放,共同催生了黔東南獨具韻味的原生態旅游。
且隨記者走進苗鄉侗寨,體味那些傳奇中的歷史名勝。
從且蘭古國到仙都鎮遠
12月2日,記者來到黃平縣舊州鎮,這是貴州古代且蘭國的國都所在地。
與夜郎齊名的且蘭是遠古的一個少數民族部落酋長國。夜郎早因司馬遷筆下的“夜郎自大”名揚四海,而且蘭卻以獨有的美麗深鎖閨中。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且蘭其實在司馬遷筆下也曾出現。
在舊州鎮,現存天官寨的遺跡,舊州古城垣的留存,歷任朝廷命官杜琢章、陳世钅庶的墓碑發現,漢印“故且蘭徒丞”的保存,以及古屋、古街、古井的大量存在,無一不佐證了且蘭古都就是今天黃平縣的舊州鎮。
當地苗、亻革群眾對舊州的稱呼“王簡”和“旺珍”,翻譯過來便是“皇城”的意思。
在黃平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廖朝圣看來,舊州是人文薈萃之地。
三國名將馬超之子馬忠是當時舊州的郡太守。
明末英雄史可法,隨萬歷年間在黃平任知州的祖父史應元,在舊州度過了一生中極為重要的青少年時期。
獨赴夷營痛斥英軍統帥的晚清名臣石贊清,也是舊州石牛寨人。
......
“這是一個歷史底蘊渾厚之地。到了這兒,時光仿佛回到了那段歷史,讓人浮想聯翩。”游客們表達著自己的感受。
第二天,我們又去了鎮遠。
“水中古城”鎮遠,擁有2281年歷史,曾設府、道、專署等七百余年,是吳敬梓筆下的“歌舞地”。
有人說,鎮遠是“中國仙都”,有人說,鎮遠是“苗疆古城”,還有人說,鎮遠是“另類江南”。而余秋雨卻說,鎮遠是“諸神狂歡地”。
從事了大半輩子鎮遠縣文史研究的縣政協文史委主任劉興明告訴記者,鎮遠占據了很多“唯一”。
這兒是貴州歷史上唯一一個把道、府、州、衛、縣設在同一處的地方。
這兒是我國目前唯一供奉戰國時期白起、王翦、廉頗、李牧四大名將的地方。
青龍洞的古建筑全世界少有,而且儒、釋、道、俗四大家和諧共處于一洞的現象更是少有。
這兒曾經是巴蜀、荊楚、吳越、閩南、中原等諸多文化交匯的地方,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多元文化現象。

清水江
讀懂清水江
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白巖松說:“我從四川的宜賓,駕車沿著長江下游行走,一直走到出海口,那段經歷讓我讀懂了半個中國。”
沿黔東南清水江一路采訪,記者也仿佛聽到了那響徹清水江畔的歷史回聲。
無論是丹寨的龍井和古法造紙作坊、黃平舊州的古鎮建筑、重安江的三朝橋、施洞的將軍府、臺江縣城的文昌宮、劍河的柳霽古城、錦屏的隆里古城和文斗古寨,天柱的70多處宗祠,還是沿江數縣的幾千塊古碑刻,幾百幢古民居、鼓樓、風雨橋,非物質文化中的侗族大歌、侗戲、苗族古歌、布依族古歌、大量文學作品和摩崖石刻,甚至連銅鼓文化、蠟染刺繡文化、銀飾及服裝文化,木商文化、宗祠文化等,都無不與清水江關聯甚密。
甚至一些即將成為淹沒區的地方,歷史也同樣在哪兒留下了烙印。
近年來,清水江下游的梯級水電開發,使得天柱、錦屏兩縣的白市、遠口等8個鄉鎮成為淹沒區或施工區。
黔東南歷史悠久,這些即將被淹沒的地方是不是埋著文物呢?人們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答案是肯定的。
2004年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專業隊伍對托口、天柱、掛治三個電站施工區及水庫淹沒區進行了文物調查、勘探工作。
雖然只是一次摸底性的初探,但考古調查組成員卻有了一次驚人的發現。
淹沒區具有重要歷史和文物價值的古代遺存共222處,其中史前遺存11處,戰國秦漢遺址1處,宋明時期遺址2處,宋墓1座,民居、廟宇和宗祠25處及大量明清橋梁、碑刻、古渡、古井等遺存。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負責人告訴記者,這11處史前遺存為探尋沅水上游史前文明提供了重要線索。他們還從仙人洞、爛草坪等11處史前遺址中采集到了大量分屬于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片。
原來,清水江流域有人類活動的時間遠不止現在所估計的,歷史又向前推進了不知多少年。
清水江邊還有一個著名的侗族村寨——三門塘,石板路、石欄桿、石頭堆砌的四合小院、土地廟、婦女井、劉氏宗祠……這一切都講述著三門塘過往的繁華。
清水江流域自古便是優質杉木產地。明永樂年間朝廷在全國征集“皇木”用于宮殿建筑,清水江“苗木”以其品質優良備受青睞,從此,三門塘成為了水運發達、商賈云集的渡口。“傳說鼎盛時期,這里木排成橋,過往行人可以從木排上直接過江,無需舟楫。”天柱縣文物管理所所長姚敦屏告訴記者。
清嘉慶年間,三門塘更是獲得了官方特許的木材貿易權,多數村民迅速轉變為木商或木行工人,逐漸富甲一方。那時若有人自外地寄信至此,只需在信封上書寫“苗河三門塘×××收”便能準確無誤地送達,三門塘名氣之大,可見一斑。
沿三門塘順河而下,便是清水江邊的另一個古鎮——錦屏隆里。
這座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古軍事屯堡因唐朝著名詩人王昌齡曾被貶謫至此而知名,更因李白遙贈王昌齡的詩句“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而聲名鵲起。
因歷史緣故,隆里現流傳下來的文化,以漢文化為主,特別以江南文化最為厚重,儒、佛、道家文化都植于這塊土地上,同時糅雜當地苗、侗文化的內容,數百年來,與當地苗、侗民族文化相互撞擊、融合,形成有別于中原文化和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亞文化群體,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文化社區。
著名學者余秋雨在考察了隆里古城后,提出這是第四種“文化孤島”現象。
清水江孕育了黔東南獨特的民族文化,有人曾經說過,要讀懂黔東南的原生態旅游內涵,首先就要讀懂清水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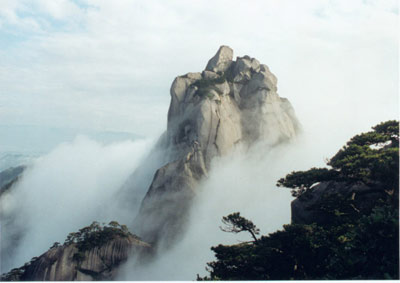
古南岳塵封天柱
湖南專家的驚天發現 古南岳塵封天柱
“古南岳塵封天柱2000多年,天柱縣境內的金鳳山就是被湖南衡山取代的古南岳。”陽國勝語出驚人。
陽國勝是來自湖南的“炎帝故里會同新說”首席專家、懷化學院座客研究員。
在多次前往天柱縣考察后,陽國勝認為貴州天柱才是中國最早的南岳圣地。
他通過收集,提出了五個方面的證據或理由。
第一,金鳳山上的乾隆題詩碑大有來頭;第二,從題詩古碑推論此南岳歷史可溯至戰國初年;第三,金鳳山符合古南岳的地緣條件并有文化淵源;第四,古南岳有緣“天柱山”,天柱縣境內正好有一座古老的“天柱山”;第五,天柱、湖南會同一帶有古南岳向外分封的傳說,古時天柱也屬會同縣。
至于,貴州天柱古南岳為什么會被歷史塵封?陽國勝認為,古稱“五溪”的湘黔邊境地區從神農時代直至戰國末期一直是人文發達之地,秦漢以后漢民族不斷南侵,土著民奮力反抗,使之淪為“戰爭窩”。戰亂造成人煙稀少,加上這一帶多為險要山地,“舊不與中國通”,使古南岳慢慢不為外界所知以至“隱姓埋名”。
這個驚天發現引起了這個“中國重晶石之鄉”的極大興趣。
“如果能夠找到足夠的證據,讓古南岳回歸天柱的話,對于我們的旅游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福音。”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楊通勇說。
在更多的天柱人看來,古南岳的桂冠如果能夠落在天柱頭上,帶來的是更多的流動人口,對于正欲打造“黔東邊貿城”的天柱而言,促進作用不言而喻。
“真是那樣的話,我們的生意更好做了。”一位百貨批發商說道。

苗疆侗土紅色文化
苗疆侗土紅色文化
黔東南厚重的歷史文化中,有一筆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紅色文化。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五次經過黔東南,轉戰從江、榕江、黃平、岑鞏等12個縣。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在黔東南留下了足跡。
而在決定中國革命、中央紅軍命運的生死關頭,中共中央在“紅軍長征入黔第一城”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否認博古、李德北上湘西與強敵硬拼的主張,采納毛澤東甩掉重兵圍堵、避實就虛、向黔北發展的意見。從此,中國革命,中央紅軍開始走上正確道路。
記者采訪時發現,在黔東南大部分縣內,都能聽到老人敘述當年紅軍的故事。
黎平縣的高屯鎮少寨,有一座著名的木橋,被稱為“紅軍橋”。當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經過少寨時,原有的木橋已被拆毀,為讓紅軍順利渡河,少寨村民冒著嚴寒,從家里扛來杉木和枋板,火把通明,與紅軍連夜架好木橋,讓紅軍隊伍繼續前進。后來人們就稱這座橋為“紅軍橋”,沿稱至今。
很多人都說:“黔東南是一個被染紅的苗侗之都。”
2004年8月19日,經省委、省政府批準,黔東南州黎平縣被劃定為革命老區;同月23日,國家發改委將黎平會議舊址列為貴州擬重點建設的“紅色之旅”景區名單。
黔東南乘勢而上,形成“苗疆侗土、紅色黎明”旅游品牌。
當地旅游部門的負責人告訴記者:“黔東南州處于全國紅色旅游"歷史轉折,出奇制勝"的重要中段。”
州委書記廖少華一直關注著紅色旅游的開發,他告訴記者:“黔東南要將生態文化旅游與紅色旅游有機結合起來,在國家大力發展紅色旅游的大好形勢下,搶抓機遇、乘勢而上,以創建"黔東南紅色旅游經典區"為目標,不斷加快紅色旅游發展步伐,促進全州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
黎平會議會址、中央紅軍總司令部駐址、紅軍銀行辦事處舊址、八舟河“紅軍橋”、榕江戰斗遺址、黑沖、冠壁山紅軍戰斗遺址、偶里紅軍書......眾多的紅色景點如星星之火,點燃了黔東南的紅色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