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新聞中心- 黔圖匯- 人才網- 視聽中心- 專題- APP

 新聞熱線:0855-8222000
新聞熱線:0855-8222000
在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考察,給予我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少數民族風情”,也不是陌生的自然和人文“風景”,而是通過對“他們”的認識,來更好地了解“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漢”和“中國”的歷史。如臺灣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所說:“‘族群’并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存在于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系中……可以說,沒有‘異族意識’就沒有‘本族意識’,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沒有‘族群邊緣’就沒有‘族群核心’。”
黔東南之旅的8 天,始終懷有一種矛盾的心情。
跟隨的是由春秋航空組織的上海作家媒體采風團,而且是最后時刻才“候補”搭上的末班車。之所以這么積極地想去,是因為近來對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感興趣,而黔東南又是著名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有苗、侗、布衣、壯、水、瑤、土家等33 個民族,每個民族內部又有各種地區和風俗習慣上的差異。

然而怎么在少數民族地區“行走”,卻一直是一個困擾我的問題。早先有朋友約我一起去西藏,我想了想,還是回絕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暫時還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姿態”。
或許我對這些問題看得過重,過于嚴苛了。這次在黔東南,沒想到,第一天,在大簸箕寨,我有些沉重的心理負擔就成功地得到“減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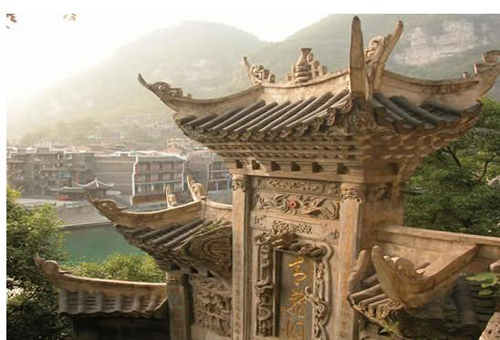
進寨前,顯然由當地相關部門進行了組織,風雨橋上攔門酒、板凳舞一應俱全,婦女和孩子盛裝列隊,男人則奏起熱鬧的苗族音樂。寨子在小河邊,沿山勢而建。經過半山男人們聚集抽煙聊天的亭子,就算進了“寨門”。看著同伴們嘩地一下散開,好奇地四處張望,相機的咔嚓聲此起彼伏,我一時有些不知所措,覺得我們一行簡直有“鬼子進村”的架勢,不僅破壞了人家日常生活的節奏,到處拿鏡頭對著人家一通狂拍,似乎也不太尊重人家(雖然他們或許不知道肖像權是什么)。
直到來到一座高高的寨樓前。寨樓有三層,側面沿外墻是木樓梯,樓梯上散坐著幾位中年苗家婦女,正在干活。真是好鏡頭啊。我忍不住,還是端起了相機。然后從相機取景框里,我看到那幾個苗家婦女正對著我指指點點,臉上笑開了花,互相唧唧喳喳說著什么。于是我也沖她們傻笑。村長正好經過,他能說一些漢語,就停下來告訴我:“她們說你比婦女還婦女。”哦,我這才明白,她們是看我的一頭長發新鮮呢,大概住在這“原生態”的苗寨里,她們很少見到長頭發男人吧。有意思的是,這一來,我的心理負擔頓時卸掉了大半—我看她們新鮮,她們看我新鮮,彼此彼此嘛。
后來村長索性帶著我們幾個,在寨子里轉悠起來,邊走邊講解那些寨樓的歷史,那一排排金黃玉米的用途,那個90 多歲還在路邊做著家務活的老婦的生平……走著走著,忽然背后一陣風,我還沒來得及回頭,另外兩位中年苗家婦女擦身而過,同時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辮子,然后嘻嘻笑著消失在小路的拐角。這下我徹底“心理平衡”了,摸都給摸了,于是端著相機,就像端著機關槍,一路狂拍過去。
凡本網注明“來源:黔東南信息港”的所有作品,均為黔東南信息港合法擁有版權或有權使用的作品,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黔東南信息港”。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黔東南信息港)”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