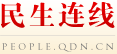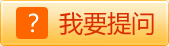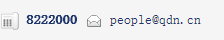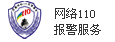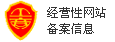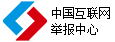吳衛(wèi)榮不是第一個走進公眾視野的被冒名者。早在2001年,山東“齊玉苓案”即引起了媒體廣泛關注——原本被某中專錄取的齊玉苓,因同學之父串通相關行政人員,這名初中應屆女生被冒名頂替長達8年。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針對該案引用公民受教育權等憲法性權利作出了司法解釋,一些學者將其解讀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不過,該司法解釋于2008年因“已停止適用”被廢止。
而一個事實是,繼“齊玉苓案”之后,由于幾乎相同的遭遇,羅彩霞、吳衛(wèi)榮等原本陌生的名字一次次被推到了公眾面前。
“冒名者的行為肯定構成侵權行為,甚至構成犯罪,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如何為受害人提供司法救濟、損害賠償?shù)姆秶鯓咏缍?這些問題就比較復雜了。”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嘯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表示。
被冒名頂替者維權艱難
對于齊玉苓而言,被冒名的8年是一段“被偷走的人生”。與其他受害者一樣,她的維權之路因冒名者“有一定勢力”而顯得艱難。
1990年,山東省滕州市某中學應屆生齊玉苓考上了省內(nèi)的一所中專。但是,同班同學陳曉琪的父親與相關行政人員串通,撤下榜單,并將女兒名字改為齊玉苓。
當時,齊玉苓家境貧窮,而陳曉琪之父是村黨支部書記。兩人的未來就此分野。
由于經(jīng)濟困難,“落榜者”齊玉苓開始了務農(nóng)、打工,并一度靠賣早點和快餐維生。與此同時,冒名者陳曉琪拿著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上學,畢業(yè)后入職中國銀行滕州支行。
據(jù)《法治周末》報道,齊玉苓1998年年底發(fā)現(xiàn)真相時,因不肯向已升任當?shù)毓賳T的陳家妥協(xié),家中陸續(xù)受到流氓、地痞的暴力騷擾。齊玉苓“不堪其擾又滿心憤怒”,次年初,她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最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陳曉琪停止對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陳曉琪及其父親、涉事兩所學校、滕州教委向齊玉苓賠禮道歉。齊玉苓還獲得了近10萬元損失賠償。
令齊玉苓沒想到的是,數(shù)年之后,一名叫羅彩霞的湖南人與她經(jīng)歷了幾乎一樣的事。
羅彩霞是2009年3月辦理網(wǎng)上銀行業(yè)務遭拒時發(fā)現(xiàn)被冒名頂替的。幾經(jīng)輾轉,她確認高中同班同學王佳俊盜用了她的身份證信息。
調(diào)查結果顯示,2004年,在班主任、高校內(nèi)部人士的共同參與下,王佳俊之父獲得了羅的身份信息、高考成績及錄取通知書。隨后,王佳俊帶著偽造的戶籍、學籍材料,以羅彩霞的名義前往貴州上大學。而羅彩霞經(jīng)過一年復讀考入了天津某高校。
地點變化加劇了維權之難。羅彩霞向中國青年報回憶,從發(fā)現(xiàn)冒名到法院開庭,共耗費了1年半的時間,“我所在的地方、她所在的地方、她工作的地方、案件發(fā)生的地方都不一樣,因此管轄權存在爭議,立案比較困難。”
在中國青年報檢索到的判決書中,“地點變化”的特點較為普遍。冒名者在甲地更換身份后,通常會前往乙地求學甚至赴丙地工作,而受害者可能又轉到丁地生活。這無疑加大了維權的時間和金錢成本。
山東、海南、河南、湖北等地公開報道則顯示,近年來冒名頂替案件,既存在領取駕照、醫(yī)保的“單項頂替”,也存在求學、入職的“完全頂替”。
在上述案件中,受害人往往時隔數(shù)年后才會發(fā)現(xiàn)身份被冒用。在訴諸法律后,他們通過法院判決獲賠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都不超過6萬元。
勝訴可能也難實現(xiàn)預期效果
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關曉海看來,冒名頂替案的判決難點之一,在于對冒名行為的定性。
他曾分析一起案例。一個劉姓青年原在河南省某鎮(zhèn)政府工作,后來離開單位前往南方打工。劉某家人認為崗位“輕易放棄甚為可惜”,便托關系安排劉某的弟弟劉二頂替其上班。三年后,劉二被人舉報“冒名頂替參加工作”。
關曉海說,劉二被以詐騙罪提起公訴,但法院審理認為詐騙罪并不成立。原因之一是,“行為人實施詐騙的主觀意圖是為了騙取財物,而劉二主觀意圖是頂替哥哥上班”。
華東政法大學民商法教研室副教授韓強認為,冒名頂替案的性質(zhì)可分三個層次。在民法層面,冒名頂替無疑侵犯了被冒名人的姓名權;在刑法層面,如果利用冒名頂替從事詐騙活動,則可能上升為犯罪行為。
“再提高一個層次,比如‘齊玉苓案’,它可以認為是一個憲法問題,被侵犯了受教育權或者某種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權利。這是一種憲法性權利。”韓強認為,對冒名頂替行為的定性,可能具有不同層次的法律意義和法律后果。
關曉海告訴中國青年報,以“齊玉苓案”為例,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賠償請求應該得到支持,但判決的難點在于如何確認賠償數(shù)額。“根據(jù)民事填補損害賠償原則,判多少才算填補損失呢?法官很難準確判定具體損失是多少。一方面,法官認可當事人權利確實受到侵犯,但另一方面,怎么救濟成為了難題。”
他坦言,賠償數(shù)額過多或過少,都可能讓當事法官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
韓強認同這種說法。他說,在冒名頂替案件中,損害賠償往往屬精神損害賠償,核算金錢較為困難。按現(xiàn)階段法院的做法,精神撫慰金數(shù)額較低,一般不超過10萬元。
在齊玉苓獲得的近10萬元賠償中,精神損害費為5萬元,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間接經(jīng)濟損失各占7000元、4.1萬余元。涉事學校、滕州教委對經(jīng)濟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其實,“賠償損失”僅是我國《侵權責任法》等法律規(guī)定的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之一。常見的救濟方式,還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恢復原狀、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及恢復名譽等。
“但是,以恢復原狀為例,有些事情可以恢復,有些事情無法恢復。”韓強舉例,對于冒名考試的情形,被冒名者能否重考、錄取資格能否重新分配等問題很難認定。尤其一些國家考試,更不太可能專門為某個當事人進行一次“恢復原狀”。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法律承認它是侵權行為,但是提供的救濟手段不充分。”韓強說,哪怕受害人獲得勝訴判決,距離其希望的救濟結果可能還相差甚遠。
身份證明制度存在漏洞
多位法學學者接受采訪時表示,冒名頂替者往往存在侵權或犯罪的主觀故意。但是,為什么屢屢有人可以冒名成功呢?
在一些受訪學者看來,問題出在身份證明制度上。韓強認為,一些單位招生、招聘工作存在信息審核、核對方面的制度缺陷,否則,即使某些人有冒名的意圖也難以得逞,更不會發(fā)生侵權、犯罪行為。
事實上,近期頻頻被曝光的“戶多多”現(xiàn)象,即暴露出人口信息登記管理制度的漏洞。據(jù)媒體披露,協(xié)助辦理假戶口的官員行政級別并不高,有的戶口甚至僅通過基層派出所就成功偽造。
程嘯說,單個身份證明材料造假容易,但一連串身份證明材料都造假的難度很大。“比如,你可能偽造身份證,但要同時偽造身份證、戶口本、錄取通知書、大學畢業(yè)證并讓它們之間相互一致的難度就很大。因此,實現(xiàn)個人身份信息系統(tǒng)的有效銜接,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冒名頂替。但目前,我國不同系統(tǒng)的個人信息之間缺乏整合。”
“另一個問題是,我國身份證明制度的信息化程度并不高。”程嘯說,目前,一些身份證明是紙質(zhì)材料,未進行信息化并聯(lián)網(wǎng),造假相對比較容易。一旦聯(lián)網(wǎng),造假就很難了。
關曉海表示,以高考投檔為例,過去紙質(zhì)封閉檔案較易篡改,現(xiàn)今電子提檔的方式確實加大了篡改難度。“但其實,冒名頂替的事情在生活中沒有減少,有時,學校老師在案件中還存在金錢等利益關系。冒名頂替肯定有一套‘操作流程’,需加強各方面監(jiān)管。”
此前,南京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還曾公開表示,關于對受害人的民事賠償,法官應充分考慮受害人被侵害的嚴重程度,對于“嚴重損及他人職業(yè)選擇、人生安排的案件”,可以判付高額的精神損害賠償金。
然而,想要證明冒名頂替者給自己造成的損失并非易事。程嘯舉例說,一名學生考上了A大學,但錄取通知書被人冒領了,第二年只考上相對較差的B大學,畢業(yè)后進了一家不滿意的單位。“你要證明現(xiàn)在的不好的處境都是由冒領者造成的,恐怕很難,因為這二者間的因果關系往往過于遙遠。”
上一篇 :廣東一法院副院長經(jīng)上級授意偽造判決書被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