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造出來的“張衡地動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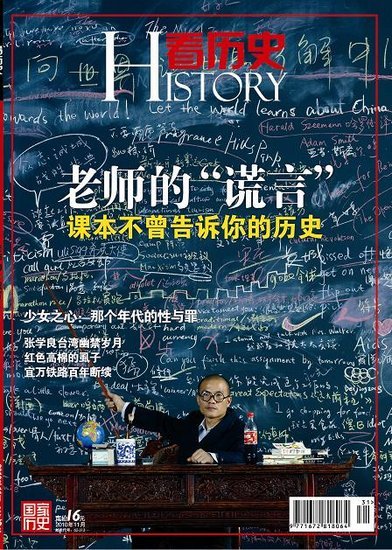
《看歷史》雜志11月刊封面

資料圖:張衡地動儀
原載《看歷史》雜志2010年第11期
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地動儀的故事誕生的時間并沒有那么久遠——直至1950年代,這個故事中的地動儀才被“制造”出來,并進入教科書中。直到數十年后,它被重新發現與“制造”。
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學生,從老師那里聽到這個生動的故事: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張衡發明了地動儀,這個地動儀像一個酒樽,內部有一個細長豎直的桿直立在正中間,地震時,這根直桿會倒向地震的方位,擊落那個方位的龍首,龍口就會張開,吐出一顆銅丸,正落在下面的銅青蛙的口中,于是觀察者就會判斷出哪個方位發生了地震。
這個地動儀的故事被當作中國偉大科技發明的典范。但大多數學生,甚至包括講述這個故事的老師們并不知道,他們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這個故事誕生的時間并沒有那么久遠——直至1950年代,這個故事中的地動儀才被“制造”出來,并進入教科書中,演變成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 王氏“地動儀”
1934年,燕京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專業的學生王振鐸誕生了復原史書中記載的張衡地動儀的念頭,他認真地研究了史書的記載,在1936年,畫出了第一套自己復原的地動儀模型圖稿。這套圖紙中,他按照《后漢書·張衡傳》中所說“形似酒樽”記載設計了它的外形,但對于內部結構,由于史料中只有區區196字,語意模糊,他遵從了英國地震學家米爾恩1883年《地震和地球的其他運動》一書中闡述的“懸垂擺”的結構原理。也就是從地動儀的上部垂下來一根擺,用以并判明地震方向,并控制相應機關。
1936年,王振鐸在第20期《燕京學報》上發表了名為《漢張衡候風地動儀造法之推測》的文章,并手繪了一套內外結構圖樣做論文的配圖。
畢業后的王振鐸擔任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設計委員,對于中國古代科技史中張衡地動儀的復原思考,不僅是他個人的愛好,同時也開始了他成長為博物館學家和古代科技史學家的起點。
王振鐸發布論文和內部結構圖一年之后,1937年日本地震學家萩原尊禮也發布了他復原的張衡地動儀論文。不同于王振鐸,萩原尊禮提出了直立桿原理,也就是在地動儀中間,放置一個倒立的直桿,地震時,直桿倒下,從而觸發相應的機關。
中日兩國在復原地動儀上的文化爭論還沒開始,兩國之間就爆發了戰事,于是,孰是孰非,就沒了下文。又過了兩年,日本地震學家今村明恒設計的地動儀也問世了,他延用了萩原尊禮的直立桿原理,并在直桿的下面放了三個彈簧,因為了有彈簧的復位工作,其原理近似懸垂擺,但問題是,至今還沒有發現東漢應用彈簧的記載。在今村明恒進行的實驗中,由于直立桿的傾倒方向與地震射線方向垂直,有悖于史書對地動儀的記載,所以,他就沒有做后續研究。
■ 獻禮
1949年新中國成立,王振鐸的新職位是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新中國在誕生之初,為了弘揚中國古代燦爛文化,國家要求博物館復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為陳列和宣傳之用。王振鐸接到的任務中,包括“四大發明”中的張衡地動儀和司南。
這一次,王振鐸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設計,根據后漢書中“中有都柱”的記載并借鑒萩原尊禮的直立桿原理,用了一年時間,于1951年設計并復原出1:10比例的木質“張衡地動儀”模型。
那是一個熱情沸騰的特殊年代,王振鐸復原的“張衡地動儀”概念模型一問世就受到了空前關注。這一肩負著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對古代科技研究和中華文明推廣普及任務的模型,成為新中國唯一一件“張衡地動儀”宣傳模型。
1952年4月號的《人民畫報》對這尊模型的成功復原進行了報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的王天木,以《偉大的祖國古代科學發明地動儀》為題,用了一個整版的篇幅圖文并茂地向讀者講解了地動儀的結構和工作原理——這一次王振鐸既否定了自己1936年認同的懸垂擺原理,又沒有繼續今村明恒的彈簧復位原理,而是將懸垂擺變成了倒立的直桿。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王天木的這篇報道清楚地寫明:“可惜張衡這一重要發明早就失傳了,隋朝時科學家臨孝恭尚寫有一部《地震銅儀經》,也未能傳流下來。”在文章的最后,還用一個段落寫道:“這里介紹的這個模型,是我們在1951年設計完成,主要是根據《后漢書·張衡傳》的記載,及考古材料而復制的。”
1953年中國郵政發行了一套主題為“偉大的發明”的特種郵票,一共四枚,其中特7 4-1是司南、特7 4-2是張衡地動儀、特7 4-3是計里鼓車、特7 4-4是渾天儀。
接下來這尊由王振鐸復制的“張衡地動儀”就被編寫進入全國中小學教科書——不同于《人民畫報》的是,后來歷次修訂的教科書中,不再提這是后人根據文獻和自己的理解復原的概念模型,一代代教師和學生就這樣認為課本上的圖片就是當年的張衡地動儀。
王振鐸也沒有想到,他的一項本職工作在作為新中國獻禮后,教育并激勵了幾代中國人,木質模型被大多數中國人誤以為是不可更改的唯一模型。在中國地方性的博物館里,王氏模型也被當作文物來仿制和收藏。不僅進入了教材,就連中國地震局也用這部復原模型做了幾十年標志,直到近年才取下。
1951年復原的“張衡地動儀”還承擔了發展對外友好的使命,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它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數次走出國門展出。它甚至作為人類文明的化身,被置于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部,而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國人從月球帶回的巖石。
■ 否定的開始
通過各種對外宣傳,外國地震學家也誤認為王氏模型就是張衡地動儀的原物。從1960年代起,這個地動儀就不斷地遭受到地震學界的質疑,這個模型的偏謬和失誤在科學實驗和理論探索的一步步深入下暴露出來。批評與否定的聲音不但對著地動儀,還直沖東漢張衡而來。
從1969年開始,日、美、荷、奧等國地震學界發表了一系列的措辭嚴厲的論文。1972年,日本學者關野雄用計算否定了直立桿原理,接下來,荷蘭的斯萊斯維克、美國人賽維于1983年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并從根本上否定了直立桿原理。
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研究、并極其推崇張衡發明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則發現了1951年模型與史書的記載不太相符。1984年,美國地震學家博爾特院士直接問過他的中國學生——從1966年邢臺地震到1976年唐山地震,總是教災區群眾“倒立酒瓶子”的馮銳,“中國人是不是很能喝酒?”在得到馮銳“李白斗酒詩百篇”答復后,大笑著說:“無怪你們的地動儀像個酒桶。”博爾特提出的問題集中在1951年模型身上:“中國目前最流行的地動儀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簡陋粗糙,機械磨擦大大降低了靈敏度,對地震的反應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應予以質疑,而且利用銅丸的掉落方向來確定震中也是不確定的”。
在全國上下都沉浸在古代偉大發明的榮耀之中時,王振鐸的老朋友、中國地震學奠基人傅承義院士當面指出了1951年模型的原理性錯誤。
那是1976年的一天,兩位老友聊天的時候談到了地動儀,傅承義說了一句,房梁下吊塊肉都比你那個模型強。在地震學家的世界里,所有懸掛物都是天然驗震器。在張衡生活的年代,人們已經習慣懸掛器物,出土文物中顯示出的編磬、編鐘、吊錘、紡線錘和吊桶、吊籃,還有吊肉和房檐上懸掛的鮮魚,都會成為這種天然的驗震器。
比這種當面批評更尷尬的是,在出國展覽時,由于沒有合理的內部結構,也沒有模仿地震的震動臺,龍口中的銅丸無法吐下來。一張1988年“張衡地動儀”訪問日本奈良時的照片,記錄下這樣的情景,中方解說在向日本觀眾講解地震儀工作狀況時,手持一根木棍,木棍捅一下,龍口中的銅丸才會掉到下面青蛙的口中。
■ 重新復原地動儀
1966年,邢臺發生地震,馮銳正在京讀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二年級。這批學生在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抗震救災并印發各種宣傳震時逃生的小傳單。其中有一條是在房間里倒立一個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地震來了,馬上出逃。
這樣的“常識”馮銳都不知道傳授給了多少人了,直到2002年的一天,國家地震局高級工程師、《防災博覽》 編輯武玉霞找到他,問他為什么在一篇科普常識中寫“地震沒地震,抬頭看吊燈”,而他早年散發的傳單卻是教人們倒立酒瓶子?前者的工作原理是驗震器的慣性原理、也就是懸垂擺原理,而“倒立酒瓶子”的原理又是什么?
武玉霞的發問正當其時,不久之后,馮銳在國家圖書館買了一本奧地利學者雷立柏的《張衡:科學與宗教》,雷立柏從哲學的角度否定了張衡,同時否定的是中國東漢時期的科學史。他認為,“對張衡地動儀的迷戀正是華夏科學停滯特點的典型表現”。
雷立柏并不了解東漢歷史,不知地動儀很可能是毀于東漢后期的戰火,所以,用他的觀點來解釋,地動儀失傳的原因,正是因為它不科學、無實用價值,所以根本沒有傳下去的道理。
武玉霞和雷立柏一個提問,一個質疑,使馮銳開始翻閱那篇用“中有都柱”等196個字來描述張衡地動儀的《后漢書·張衡列傳》,專業地震工作者的優勢在于,他可以根據“圓徑八尺”(八漢尺,一漢尺等于23.5厘米)這個范曄留下的數據,做倒推計算,算出都柱的高度,而這個高度只能是一個懸垂擺,而無法是一個直立的桿。
科技史學者一般是用建立在數理統計、數理模型上的地震學理論去驗證自己的假設。用這套理論,能把各地震臺網搜集到的真實震力轉為地震波型,再將波型轉化為數據。而馮銳卻是從數據開始,去倒推出了地動儀的工作原理。當數據與理論吻合時,便證明了懸垂擺的合理性,圖紙上的復原可以結束了。
2003年,河南博物院決定在官網上張榜招賢,讓張衡的地動儀真正能動,不要再通過人為控制進行“表演”。
于是,馮銳的團隊擴大了,文史界的參與,使得“孤”證《后漢書》不再孤立。文史學者在比《后漢書》早的《續漢書》,以及《后漢紀》等七部古籍中找到了更多關于張衡地動儀的記載。196個字的記錄,變成了238個字。
通過這些文獻,馮銳他們算出了張衡地動儀的高度、懸垂擺長度、震蕩頻率等。與此同時,課題組調來了隴西地震的歷次波形圖。通過對波形圖的計算,證明張衡的地震儀在公元134年的確測到了隴西的地震。張衡地動儀不再是“傳說”和“神話”。
■ 糾偏
復原古代科技模型的幾個途徑中,文獻記載詳細并存有實物的,復原出來最為真實;另一種情況是,只有文獻記載,但實物早已失傳。而王振鐸和馮銳共同面對的,都是沒有實物參照的問題。
不同的是,王振鐸只能通過文獻進行單槍匹馬的探究。而馮銳由于專業優勢,在參閱文獻的同時還有地震理論及數理計算來幫助他尋找真相。加上后來成立的課題組,使得馮銳的復原工作進行得更為合乎科學邏輯。
馮銳復原的地動儀于2009年9月初小學開學不久,安裝在北京市重點學校史家小學,這家學校的校長黃守圣說,在考試的時候,會要求學生今天按照正確的答案回答,而非教材上要求的那樣。
此時,全國中小學教材在講到地動儀時還是幾十年一貫的倒放一根“直立桿”理論。而馮銳已經多次與人民教育出版社溝通,最初得到的答復是需要地震局的證明文件,但當看到最新修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對于“張衡地動儀”這一詞條已經做出修正,人教社便準備在2010年有所改動。
2009年9月20日,中國科技館新館開幕,地動儀在新館與觀眾見面,并在震動儀模擬的地震波中進行吐丸的工作。觀眾可以親自動手按下按鈕,觀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動儀的不同反應——只有橫波到來它才吐丸,其他來自縱波的震動,都無法使地動儀有任何反應。這就排除了其它的干擾,如很重的關門、汽車過境的震動、巨大的炮聲等。
美籍華裔理論物理學家、國際華人物理學會會長楊炳麟,訪華期間聽了馮銳在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做的報告會后,認為從這部機器上可以看出,張衡應該是最早利用慣性原理的驗震的人,這是物理發展史中的里程碑。
2010年1月24日,馮銳接到教育部長袁貴仁的電話,袁貴仁在仔細閱讀馮銳修改教科書的建議和相關資料后,原則同意修改“張衡地動儀”這一章節。2010年秋季教改出臺以后,按照教學大綱,“張衡地動儀”已不再是歷史課本中的內容。人教版歷史課本中已拿掉了這一知識環節。作為對這一錯誤的補救措施,人教社今后會將新版地動儀的知識加到教師用書中。
2010年開幕的世博會將張衡地動儀新模型列為展品之一,中國政府也將馮氏原理的張衡地動儀,納入“中國古代機械成就展”這一全球巡展之中。
對于這座再次震動了地震界的“張衡地動儀”,馮銳認為:“只能說它是我們在當前這個時代對張衡的理解”。他希望未來還會有人能夠超越,能夠更加接近張衡。





